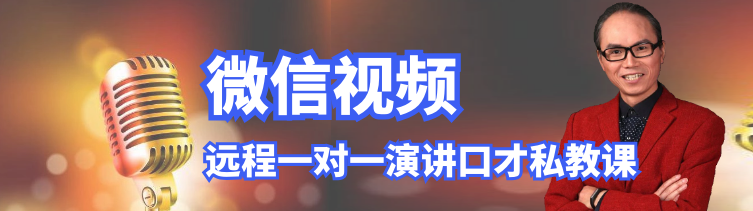华东师大教授:我想说的话越来越多,我能说的话越来少
我时常会想,如果一个社会对立加剧、戾气横行,如果容错率降低、极端事件频发,撇开其他原因,是不是也因为我们遗忘了先贤们关于仁爱的叮咛呢?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教授在2023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仁 者 不 忧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早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热烈祝贺各位同学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每年站在这里,我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一个多世纪前,卡夫卡写信给他妹妹说:“我写的不同于我说的,我说的不同于我想的,我想的不同于我应该想的,如此下去,直至最晦暗的深渊。”
其实同样,在我们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想要说的话越来越多,但是我能说的话越来越少。我张口的时候,总觉得空虚,因为常常言不及义;而我沉默的时候,也并不觉得充实,我常常因为不能仗义执言而心怀愧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句话说得口滑,就会被网上的好事之徒断章取义,自己就会堕入幽冥的深渊。
我最近一直听说,在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之际,等着我们的是浪急风高甚至惊涛骇浪。如果时代向我们提出了底限思维的要求,我当然会隐隐然担心,将有什么大的坏事情发生。
现象级灾难其实已经发生过了,比如新冠疫情。我曾经too simple too naive地相信,该死的瘟神送走之后,我们的经济会迅速逆转,超越三年前的发展水平。但很遗憾,现实很骨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四月,24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率突破了20%。即便是我们国汉院,就业率也不再能回到原先百分之百的那种持续辉煌。
虽然我深信,诸君未来肯定会幸运地摆脱灵活就业的命运,但很可能我们的微薄薪水配不上我们的消费激情,我们的工作条件配不上我们的事业雄心。如果内卷的竞争过于残酷,如果996的压力让人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们有什么资格谴责人们把小确幸当成人生的大目标呢?
两个多月前,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说,网约车太多,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客源,如果不将工作时间延长到极限,比如十二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就无法在缴纳公司管理费之外有所盈余。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在高速路上看到一位出租司机边慢吞吞开车边打瞌睡;他还告诉我,有一次由于解决内急而来不及按规定停车,被罚款二百,他忍不住嚎啕大哭。
也许,这样的悲剧日常只是发生在小部分人身上的极端。但是,展望未来之路,有几人能够鲜衣怒马看遍繁花?又有几人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李白曾经慨叹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谁能向我们保证,这样的人生浩叹我们可以无需重演?
很抱歉,在同学们庆祝毕业的大喜日子里,我不合时宜地跟大家说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当然祝愿而且相信所有的同学们会前程似锦。但不管怎么说,忧患意识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血脉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文学从业人员,我认为文学的优点在于提出问题,而缺点在于它不负责解决问题。但如果我们作为书生不能进入社会机制内部,不能现实主义地解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宏大问题,我们依然可以积极地考虑解决个体的焦虑问题。
这里我斗胆推荐的一款疗治时代忧郁症的药方,或者一道让人安身立命的心灵鸡汤,就是孔子的教导:仁者不忧。
这个命题简单来说就是,无论穷达,尤其是万一我们处境窘迫,我们还是要坚持做一个仁者,由此我们试图达到不再焦虑的境域。讲到这里,我要嘚瑟一下,我去年获评了上海市“四有好教师”的提名。虽然是个提名,当然意味着我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但重要的是,我欣喜地发现,“四有”中的一有即“有仁爱之心”,如今是党和国家现在所提倡的积极价值。
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孔子是孔老二,仁爱是被批判的东西。老师告诉我们,元宵节的灯会活动,是宣扬封建迷信的活动,应该予以无情打击。我就伙同小伙伴,捡了一些瓦片,看到比我更小的儿童兴高采烈地拉着兔灯,就商量好了一起投掷瓦片,迅速逃跑。然后躲在远处,看到焚烧的兔灯和孩子哭泣的声音,顿时就有点后悔,但内心另一种声音很快制服了我:我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不能压倒小资产阶级的人情。
老师教育我们,要严防坏人坏事,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要汇报。有一回我在如城的北门大桥上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时不时东张西望一番再低下头做些什么。我心惊胆战地跟踪过去,突然发现有一股轻烟冒出来了,我立刻意识到阶级敌人试图炸毁大桥,于是不顾一切,一个箭步扑过去,结果发现并没有发生同归于尽的爆炸事件,人家其实是在吃烤红薯,他只是吃东西不想被人发现。
这是我童年时期对社会世界的感知方式。不过,对陌生人的普遍怀疑,不一定始自当代。明人洪应明《菜根谭》中有一句名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表达了这层意思。
我们的处事哲学好像是,假如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但假如你对我并无滴水之恩,我又何必对你亲近信任?当然,我这里绝不是说,对于境内外敌对势力,我们还可以假以辞色;敌人来了有猎枪,对他们我们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但是,如果我们想构建和谐社会,想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我们就不必每一分钟都绷紧神经。
即便在烽烟四起的春秋时代,孔子还要求弟子们“泛爱众而亲仁。”即便命途多舛,陶渊明还吟诵出“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诗句。我时常会想,如果一个社会对立加剧、戾气横行,如果容错率降低、极端事件频发,撇开其他原因,是不是也因为我们遗忘了先贤们关于仁爱的叮咛呢?
那么,什么是仁爱呢?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道即仁,也就是忠恕。根据传统的解释,忠是中和心的合成,朱熹说:“尽己之谓忠”,就是《礼记•大学》中讲的诚意正心,换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守住我们的初心;恕,是如和心的合成,朱熹说:“推己之谓恕”,不是指宽恕,而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这让人油然想起康德著名的绝对律令:“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但是,在人的本性中,利己的冲动远比利它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因此,仁的实践似乎是难的。如果我们看过韩国的电影《寄生虫》,我们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家里有余粮的地主,比处在窘迫的生活压力之下的底层人民更容易好善乐施。
但这并不是孔子的看法。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们未必有能力改变外部世界,但仁爱,我们依靠自己的主观意志还是可以接近的。孔子赞扬他首座弟子颜回的话我们大家都是熟知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仁者而言,不仅贫贱不能移,而且履仁蹈义本身还能获得至乐。
根据新儒家徐复观先生的说法,仁者之乐,来自于义精仁熟,来自于对社会责任的慨然担当,来自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挥洒自如,来自于生命力量的跳跃与升华:因为在践履仁爱的过程中,人的精神超逸出身体自然的约束,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从而自己的心性境界得到扩大,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安顿和圆满,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会说“吾与点也”,为什么会告诉我们“仁者不忧”。
但仁者的果位,连孔子也自认为难以企及,那为何我还要向大家提出这样似乎不切实际的建议呢?
我想引用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
“圣·奥古斯丁的一个门徒波林纳斯敦促诺森布利亚国王爱德温改宗基督教这种新的信仰。国王召开一次会议,问计于他的谋臣们。其中一人直言道:‘王上,人的一生就好像您冬天在宫中用餐时,突然飞进宫殿来的一只麻雀,这时宫中炉火熊熊,外面却是雨雪霏霏。那只麻雀穿过一道门飞进来,在明亮温暖的炉火边稍停片刻,然后又向另一道门飞去,消失在它所从来的严冬的黑暗里。在人的一生中,我们能看见的也不过是在这里稍停的片刻,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一切,我们都一无所知。要是这种新的教义可以肯定告诉我们这一类事情,让我们就遵从它吧。’”
我不是基督徒,当然不会规劝大家皈依基督教。作为无神论者,我也不相信基督教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坚实可靠的确定性。但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前面的道路究竟如何,我们是茫然无知的。但如果我们立志于做一个仁者,我们可以无待于外物而追求内心的澄明和对他人的关爱,我们就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为自己树立了确定性,这不再是小确幸,而是怀抱信念的大欢喜——是否达到仁者的某种段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仁爱的大方向。
由此,我们也战胜了焦虑和烦恼,我们可以不怨天、不尤人、不疑惧、不忧郁。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同学们,祝福你们!谢谢!